
原创 看理想节目 看理想

例如二战的时候,纳粹德国新建了很多集中营来囚禁犹太人,在里面对他们进行毒害与虐待的时候,集中营整个国家机器里面的那些小官僚、所谓的技术官僚到底有没有责任?
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就是有个人说:我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听希特勒的命令。
上级给我的命令是,你现在去建个集中营,按下按钮把那些犹太人毒杀,那我就应该要做。因为如果我不做,我拒绝上司的命令,拒绝服从这个体系,我就没有尽到我的责任。
但是作为旁人的我们肯定会认为,这种行为其实是在杀人,你难道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吗?怎么会把它理解为个人在体系里有没有服从命令的一件事?
所以关于这一点衍生出了很多的讨论,也就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件事情的背景。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并不陌生,自古以来,在一些重大的政治灾难或者历史变动的时刻,也有很多人参与了一些事情,他可能都会觉得我只是负责其中一小部分,我其实不属于罪恶体系的一份子,怎么能说“我有罪”?
在看理想App周年庆的「我没有杀人,我只负责按钮」专场,梁文道、詹青云、庞颖、徐英瑾共同探讨了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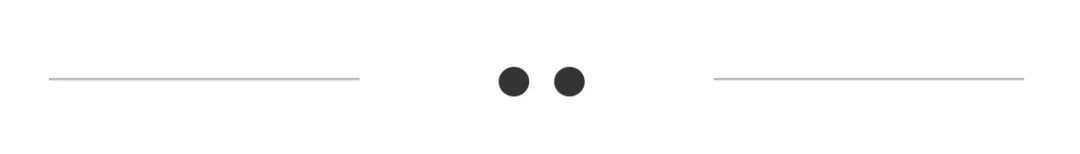
徐英瑾:平庸的恶里有个人自由的空间
你愿意在里面混,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你还没有被所做的事情的道德性质所震撼到,你没有意识到按一个电钮失去这么多生命这件事,在道德上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你的道德感已经被钝化了,所以这个责任还是由个体来付的。
首先从哲学角度上讲,这牵涉到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自由和体制的必然性之间的一个关系。很多人要用平庸的恶为自己来打掩饰,说“我是在这个体制里面吃饭的”,但是在纳粹德国时期很多人就不吃这一套。
比如在纳粹德国的时候,所有大学的老师都必须加入纳粹的,你如果不加入纳粹党,你就没办法有教职了。
但是有些人是在纳粹上台之前就加入纳粹党了,比如说海德格尔;有些人应该是纳粹上台以后加入纳粹党的,比如像伽达默尔。我们一般来说,对海德格尔是不原谅的,你加入也太早了,对不对?伽达默尔就算了,大家混口饭吃。
但也有人他始终不加入,因此丢了大学教职了,也没被饿死,比如说雅斯贝斯。我们说的轴心时代就是雅斯贝斯提出来的。因此在事后我们在这些人的道德评分里面,对雅斯贝斯的评分,就相对来说比较高。
这就证明什么?就证明了你是有选择的。很多人都觉得在这种集权的体制下面,咱们要选择反抗,就一定要像施陶芬贝格伯爵一样,拿个炸药包跑到希特勒旁边把他炸死。
要求不是特别高,你像雅斯贝斯那样,我就借个口,不上你的这个班了,我回家住在家里面,种种菜我也饿不死。
所以你如果作为一个党卫军的一个成员,你首先要知道你加入党卫军本身要干什么。但是如果本来是受一些政治蒙蔽,然后突然在某一个环节发现好像没有你说的那么好,你如果真想脱离这个体制,真是有很多很多的办法。
你愿意在里面混,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你还没有被你所做的这个事情的道德性质所震撼到,你没有意识到这按一个电钮失去这么多生命这件事在道德上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你的道德感已经被钝化了,所以这个责任还是由个体来付的。
萨特也指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自由可以说是人的本质性的一个根本特点。这个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如果你真的想办法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的话,即使你被囚禁在监狱里面,你都有一个很大的方向。
同时还有一种观点为平庸之恶做一个辩护,就是说这个社会的个体很大,咱们每一个个体都像一粒沙子一样的,如果我不做这事儿也有别人来做。
这里我有两个观点了:第一,别人做,至少你可以不做了。你不做了,至少对你的好处是,你摆脱了这个道德责任了,或者说你下半部辈子不用受这个东西的煎熬了。
其二,你不要小看个体的作用,咱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是非常奇怪的,到处充满着很奇怪的蝴蝶效应,不知道哪里蝴蝶啪啪啪一下子,就会引起加州的风暴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智利人仅仅因为三美分的地铁票涨价就会闹得那么厉害。
所以你看看现在的互联网上有一些群体性的事件,它最先爆发的这么一个点可能也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你反过来想,如果你愿意在某件事情上做出某种不妥协的态度,影响了一些人,它能够得到的那个后果有可能要比你预想的要来的大,因此你就可以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引发整个社会的一个变化。
我就记得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是法国的一个中年妇女在街上喊面包没了,然后就全部爆发了,她也没想到她随便喊一嗓子,就让法国的整个政治制度产生了一个颠覆性的影响。
那么说到这我大致就亮出了我一个观点,平庸的恶,它背后是误解了人类的自由空间的广度和深度。
2.
庞颖:在行恶之前,我未知恶是什么
善恶的钝感、道德的钝感,有多少究竟是我们个体的错?如果它是一种群体性的道德钝感,有多少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有多少是环境把我教育、把我洗脑成了这样?
我先从一个故事说起,《黑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其中有一集是这样的,开场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美国大兵在射杀丧尸,这听上去是一件非常正义的事情,对不对?但后来发现那些人并不是真的丧尸,而是大兵们的脑子里面被植入了一个芯片,他们看到的所谓丧尸其实只是非法移民、政治敌人,或者是犹太人——在我们的这个故事里。
所以这些大兵看到每一个人,在杀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本能性的不适。但是这些大兵的政府,这些大兵的领导,他们对这些大兵进行洗脑也好,其他的方式也好,让他们看到的是一群邪恶的应该被杀死的人。
放到我们今天这个例子里是什么?是钝感,善恶的钝感、道德的钝感。
有多少究竟是我们个体的错?如果它是一种群体性的道德钝感,有多少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有多少是环境把我教育、把我洗脑成了这样?
如果我从小生长的环境里,我就被教育屠杀犹太人是一种清洗,是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我有一个高尚的目标,为了结果正义,我必须要牺牲一些程序正义,我或者是为了结果、正义宏大的目标,我必须牺牲掉一些数字,做一些事情。
如果是渲染这样一些口号,变成了隔着我的内心或者隔着我的良知和杀人之间的一道屏障,它让我产生这种钝感,这到底是我个人的错,还是说我不幸生在了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我以前是做公务员的,在我去找这份工作的时候,没有人要求我要懂哲学,没有人要求我要懂法律。请问我今天做了我一个公务员的本分本职工作,我需要去考量这整个国家的法律是符合正义的吗?
在纳粹德国的状况之下,我做的事情很有可能是符合这个国家的法律,我甚至还得必须超越国家的法律体系,站在一个更高阶的程度,去站在一个外人的角度,去评价我这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是不是正义的,我要不要遵守它。
我觉得这对一个公务员的要求可能有点太高了,你让我做这份工作之前,你没告诉我,我必须会这个。我今天没做到这个,你就说这是我的错。
其实从立场上我也认为平庸之恶是恶,我也认为按钮是恶,但是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需要充分考量两方。
如果我站在这样的角度下,是环境、是教育、是那些宣传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它隔绝了我的良知和杀人,请问这件事情究竟是我个人的问题,还是环境的问题?
3.
徐英瑾:知恶是一种人类的本能
我们称之为人性的东西,很可能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心理学,甚至是生理学的基础,也就是我们的同情心。
《黑镜》电影里面的科幻场景和我们说的纳粹德国的洗脑其实有点不一样。
因为科幻场景如果真的出现的话,美国士兵不是被教育成把非法移民看成是丧尸的,他们的大脑已经在生理学的层面上被改造过了,他的确看到的就是丧尸。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大脑本身已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改造了,把人都看成鬼或者其他情况,这时候他朝鬼开枪,基本上我们认为在道德上就不应该由他负责,而是应该由执行计划的人负责。
但是洗脑只是一种非常粗疏的讲法,因为我是研究语言哲学的,会知道有很多类似的字眼,有时候给大家造成了一种错误的类比,比如洗脑和洗胃这两个词是很像的,但是洗胃是个生理学过程,洗脑不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
洗脑本身是通过大量信息的轰炸,以及有意地屏蔽另外一部分与之不同的信息,诱导你接受了某一方面的信息。
它为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和洗胃不同呢?洗胃被洗了也就洗了,你说我抵抗,我不洗,胃是不受你控制的。但是洗脑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因为谎言总有谎言的一些痕迹,它总是会在某些地方暴露出来。
纳粹在进行洗脑的时候喜欢放一部电影叫《犹太人苏斯》——大家可以去看看,我自己是被这部电影吓到了,因为拍得非常好,对于当时纳粹宣传部门怎么控制艺人,做出了一个很精密的讨论。
但是所有的洗脑都有缺点,包括那个被控制的艺人,他一直在进行天人交战,当他发现自己教育出来的孩子已经不受他自己的控制,开始唱纳粹所谓的青年团的团歌的时候,他就觉得下一代已经被毁了。
甚至包括所有一切的始作俑者希姆莱本人,有一个史料说,希姆莱有一次在看手下枪决犹太人的时候,血浆溅到了他的身上,他差点吐了,然后产生了非常像我们正常人的心理和生理反应,因此他就说,以后不许用这种方法杀死犹太人,太残忍了,想来想去用了毒气。
也就是说,即使是这样的人,他身上都存有一点点人性的成分。这也就证明了我们称之为人性的东西,很可能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心理学,甚至是生理学的基础,也就是我们的同情心。
我们看到类似于和我们长得一样的物种,不要说犹太人是我们人类了,即使是黑猩猩这样的物种,看到我们在残杀它们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不忍,何况是人?
这样一种原始的机制存在,除非你在生物学上把它阉割掉了,否则它的存在就可以构成我们的道德行为最保底的力量。
4.
詹青云:区分平庸之恶里的善恶与思维能力
我们今天作为后人去看待那个更广阔的图景的时候,会说太残忍了,太可怕了。我当然觉得这当中的每一个参与者都是恶的一份子,可是我身在其中的时候,如果我只看到我这条路,你能不能够指责我说,你为什么没有看到那个更大的图景?
为什么纳粹德国给我们这么大的冲击和反思,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德国是一个拥有贝多芬的民族,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人道主义文明世界以后,依然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情。
那么又为什么提出平庸之恶这个概念?这件事情的可怕,不是他把人变成了非人,变成了沦丧道德感的人,然后每个人去做很残忍的事情,而是他把恶变成了一个国家机器。
每一个人在屠杀当中扮演的角色都不是赤裸裸拿刀刺进去,然后看着血流出来还能够笑出来。
平庸之恶这件事情的可怕之处在于,每个人都在这场洪水当中扮演了一滴水,他可能不知道我是这场洪水当中的一滴水,这才是平庸之恶可怕的地方。
他不是把每一个人变成恶人,他是把一个体系里的每一个人变成这个恶的参与者,然后大家还浑然不觉。
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探讨的是两种问题,一是一个人的底线可以有多低,人是不是能沦丧到对于同类之间那种起码的人与人的感应都没有了。而距离感的意思是说,我就是感受不到,我只是这个环节当中的一部分。
如果我只是纳粹的一个工人,我是建造这个集中营的搬砖工人,我还是运送这些犹太人的卡车司机,我都在这场屠杀当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可是我知道还是不知道我是在参与这种恶,做它的一份子呢?
这个时候我们对人的另一个衡量的标准是,我们对这个人的期待有多高,一个人身处在这样环境之中的时候,他所看到的眼前的景象有多大。
如果我是这个卡车司机,我是只看到我面前的这条路,我有一个义务是运送一车人到某一个地方去,还是我要跳脱出这条路说,我运送这一车人是运送他们去死,还是我更跳脱一层说,我运送这车人去死,是我在参与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种族屠杀。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要求每一个普通人都跳出他眼前的这条路,去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我们今天作为后人去看待那个更广阔的图景的时候,我们会说太残忍了,太可怕了。我当然觉得这个当中的每一个参与者都是恶的一份子,可是我身在其中的时候,如果我只看到我这条路,你能不能够指责我说,你为什么没有看到那个更大的图景?
这两种指责是不一样的。一种指责是,如果我看到了我还这么去做,这是一个选择;另一种指责是,我跳脱不出我身处的这个环境。
这种指责不是善恶的指责,它可能是一个人的思维能力的指责,那我们能不能够把这种对于一个人所看到的图景有多广阔,他的层次有多高的指责,上升到善恶判断呢?我觉得这才是问题所在。
5.
梁文道:当我放弃人性,我才好安顿我的心情
在更常见的一个大时代的政治灾难底下,所谓的帮凶或者共谋,大部分人本能的反应是,我干嘛要管那么多事,这不关我的事。
像刚才詹青云提到那个例子,假设我是帮忙集中营去搬砖的人,我是不是有责任要知道我搬砖去建的房子,最后要用来做什么呢?
比如说今天随便一个建筑工人,我们是不是都需要他知道这房子最后要干吗?
原来这个房子最后是要用来干一件坏事的,比如说是一个毒贩的窝藏毒品的地方,那他是不是需要知道这个?假如他真的不知道,那么他有没有责任要去知道?这种知道的责任到底有多大?这是一个问题。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更符合人类常见的一种情态是,很多人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一些什么,但是反而希望让自己不要弄清楚。
比如说这份文件是个杀人名单,我的老板递给我了,让我去搞定一切。我的确大概猜到我们在做什么;那边在盖集中营了,我也模模糊糊知道一点,但我不想看得那么清楚。我只是一个负责传递文件的文员,我交过去就是了,这关我什么事呢?
所以在更常见的一个大时代的政治灾难底下,所谓的帮凶或者共谋,大部分人本能的反应是,我干嘛要管那么多事,这不关我的事。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反应,其实从逻辑上讲我们不能说不关他的事,可是他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关我的事”的那种状态下,才能舒适地去安顿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去继续工作和生活。
所以所谓的一个人放弃思考,那种放弃是哪一种状态呢?
是他根本没有能力去思考,还是说,是他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什么,但他抗拒对这件事情下判断,抗拒承担责任,哪一种情况更多?
6.
庞颖: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傻白甜地活着
我们来讨论平庸之恶的概念,目的是什么?是告诉我们自己,提醒我们自己,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多想几步的。
我自己认为,在当今的社会中保持独立思考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们上场之前跟道长聊天,道长说他八几年去美国的时候,觉得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像是没有明天一样,在厨房里擦桌子不会用抹布,会用纸。
包括他们买东西是很便宜的,但这些便宜来源于哪儿,可能一双很便宜的球鞋,来源于东南亚的血汗工厂。
你会不会认为东南亚血汗工厂里的那些人,是你需要关心的人?我是关心人类,我是对人类有同理心,但我不认为以前的白人,会认为黑人是属于人类的一部分。
包括现在你要有同理心,东南亚那些血汗工厂里的人,是不是你需要关心的?之前节目里面也讲到美国工厂,我们现在追求效率,我们追求更加便宜的价格,我们总觉得又方便又便宜的服务特别好。
但其实你多想几层,你会想到羊毛总要出在羊身上,总是有人牺牲了一些东西,比如牺牲了他的安全,牺牲了他的生活等等。
在我们在已经构建好的社会体制里面,想到这些东西,为这些东西负责,或者是试图做什么去改变这些东西是很难的。
我一个人拒绝消费,可能不会改变什么;我一个人振臂高呼,可能也不会改变什么,这个要求是很难的。
但是我们来讨论平庸之恶的概念,目的是什么?是告诉我们自己,提醒我们自己,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多想几步的。
在我们那种隐隐约约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其实是保护自己柔弱的内心,如果我想太多,我会觉得我穿这双鞋可能有人在血汗工厂,越南小孩在打工,没有学上,对吧?我改变不了什么,我内心又很痛苦,这个时候一种选择就是,我一个人改变我的行为改变不了什么,所以干脆不去想。
另外一种选择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做什么,一个人改变可能不能改变什么,但如果我们每个人,每个人都做一点什么,兴许这个世界会改变。
又或者,哪怕什么也改变不了,我心存敬畏之心,心存愧疚之心,这样的一种道德感是不是应该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
一种是“傻白甜”地活得很快乐,一种是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你选择做哪种人,可能是我们亟需的一种反思。
